2016年3月25日下午,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行政管理研究所在蒙民伟楼246会议室成功举办系所3月份的第二场seminar。杨鸣宇博士以“公众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基于中国环境抗争事件的研究”为主题做报告,学院、系所相关专业老师、博士、硕士研究生等三十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众所周知,公共政策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日益显现。杨鸣宇博士基于案例比较和QCA的方法,以环境抗争事件为切入点开展研究,将已有成果按照“‘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发现和假定”、“既有研究局限”、“案例收集与QCA研究方法的优势”、“QCA结果和解读”、“威权政体的信息问题”、“结论”六个部分一一呈现,旨在阐释碎片化权威主义没有办法解答的一些问题,探究体制外的行动者影响政府政策结果的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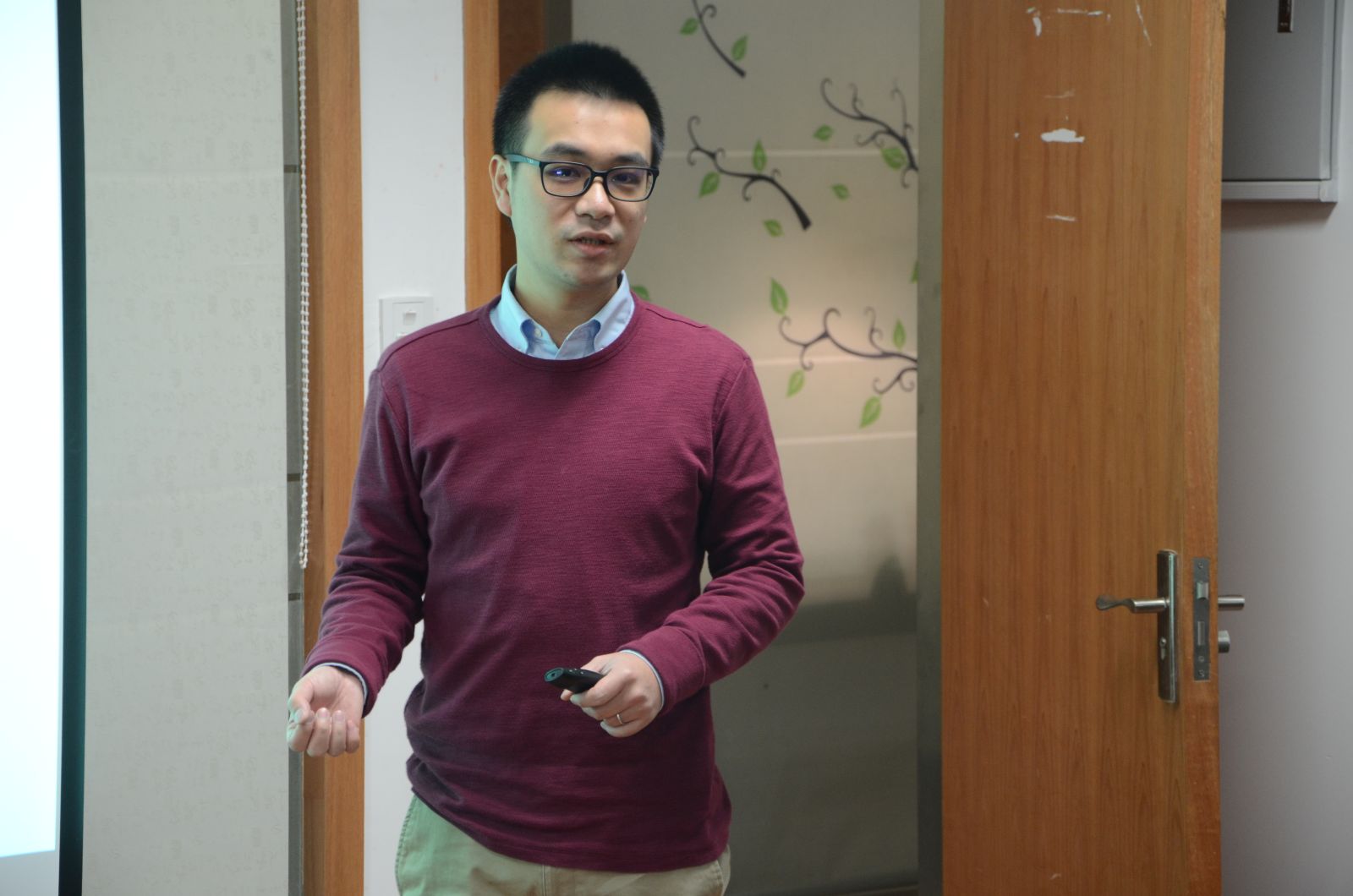
首先,杨鸣宇博士介绍了“碎片化权威主义”的发现和假定。著名学者Lieberthal.K和Oksenberg.M编写的《Policy Making in China》一书对我们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主要有三个发现:碎片化的权力结构、共识的建立与离散的决策过程。同时,该书还引申出两个推论,即“体制内”的行动者拥有绝对话语权,导致部门利益协调困难。然而,怒江水电站缓建、PX项目搁置等事件均表明,碎片化威权主义制无法解释一个重要的议题:为何体制外的行动者可能改变政府的政策结果?
其次,杨鸣宇博士概括了既有研究的局限。Andrew Mertha在《China’s Water Warriors》中把Policy Entrepreneur的概念引入中国政策过程的分析中;《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两本著作证明了游行也是改变政策结果的方式之一。然而,以上研究均存在一个缺陷:它们没有考虑负面案例(negative case),缺乏类似案例间的对比。此外,如何知道民意在政策结果中产生了作用?毕竟决定整个协商过程以至最终结果的仍然是政府;即便民意真的发挥了作用,但协商式的决策也只是极小范围内的政策试验,而不是常规的决策程序。
然后,杨鸣宇博士介绍了本次报告的样本搜集与研究方法。他利用新闻报道搜集了25个环境抗争事件,运用QCA方法,考虑了是否有环保NGO或专家学者的参与、是否有媒体进行过报导、是有人数在500以上的游行等6个可能影响政策结果的因素。相比量化分析方法(比如回归),QCA方法具有如下优势:第一,特别适合用于分析小型或中型样本量(10<N<100);第二,容许研究者找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第三,容许研究者找出导致社会现象发生的多条路径。
接着,杨鸣宇博士向与会者呈现了QCA结果。体制外的行动者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改变政策结果:第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专家诱导”。典型案例是怒江水电站和厦门PX事;第二条路径可以称之为“游行诱导”。典型案例有什邡事件、上海金山PX等。
随后,杨鸣宇博士提到了威权政体的信息问题。他认为,威权政体相比民主政体更可能隐瞒和操纵信息的公开和流动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政府可以在政策过程中保持主导地位;第二,通过隐瞒和操纵信息,一般人很难准确评估国家的状况和政府执政表现,从而减少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中央政府在主导了信息自上而下流动的同时,也妨碍了它自上而下地接受来自社会的信息反馈,这增加了作出错误决策的可能。
最后,杨鸣宇博士就本次报告进行总结。报告主要有4个结论:第一,“专家诱导”和“游行诱导”是两条体制外行动者改变政策结果的基本路径;第二,上述两条路径发挥作用的机制在于:新的政策信息被引入,使得新的政策利益相关者出现,打破原有政策系统的内部平衡。同时,释放出强烈的社会不稳定信息,使得政府意识到回应民意的迫切性;第三,中国和民主政体在政策变迁的路径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相反差异的地方在于信息反馈的渠道;第四,理论上威权政体的信息问题会使政府不敏感于社会变化,政体容易出现不稳定,而中国却是一个理论预期外的例子,可能原因是中国的央地二分政治结构。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关注这样的权力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有助缓解信息反馈不足的问题。

与会人员对杨鸣宇博士的“公众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基于中国环境抗争事件的研究”的主题报告提出以下问题及点评意见。
高翔博士点评如下:本次研究的选题非常重要,研究方法也很规范,给出了“专家诱导”和“游行诱导”两条民众影响政策结果的路径,并且将之放在威权政体信息的框架下加以解释。同时,高博士提出了三点疑惑:第一,Andrew Mertha考虑了正反面案例的对比,本项研究对过往文献的判断需要更加审慎;第二,研究的自变量是6个可能影响政策结果的因素,因变量是政策结果改变与否。那么,提出这6个自变量的依据是什么?Mertha考虑的“议题塑造的类型”等要素在本项研究中没有得到体现。另外,如何判断是否改变了政策结果?可能出现短时间搁置项目,最终政府仍然执行政策的情况;第三,将两种路径放到威权国家信息获取的框架中固然有对话的优势,但不免存在忽视其他影响要素的嫌疑,使得模型结论的解释力降低。
对此,杨鸣宇博士回应道:对于民众成功改变政策结果的判定标准有两个:政策最终完全改变(如厦门PX搬到漳州)与延误、搁置。而专家如何定义事件的性质体现了Mertha考虑的“议题塑造的类型”。至于其他要素发挥的作用,我们确实应该正视。比如厦门PX与杭州PX项目,是否由国企投资导致了很大的结果差异。
吴金群博士提问:杨博士提出的影响因素可以视为研究假设,在运用QCA方法后有没有进行统计检验,不同的假设排列是否会导致得出的结论不稳健?杨鸣宇博士回答:个人认为统计检验在本项研究中并不是那么重要。QCA方法与定量研究不同,它的逻辑起点否认单一因素会影响社会现象的发生。所以本研究是基于个人的开放理解,从诸多案例中简化出一些影响因素的组合排列,提供逻辑上的简化,尽可能得出一个很简洁且解释力较强的结论。
陈丽君博士提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大量政策进行了变革,其中有多少变革是通过抗争性的案例导致的?如果这个比例很小,那么通过极小部分的案例诠释整个中国政府的政策演变是否合适?高翔博士补充:陈老师的问题涉及研究问题的定位。体制外参与者有很多种途径影响政策,这项研究更精准的定位应该在于:当民众采取环境抗争的方式时,什么样的条件会影响政策结果。
杨鸣宇博士回应道:本项研究并非想概括整个中国政策变迁的过程。研究的起点是希望阐明既有模式无法解释的少数案例。
田传浩博士提问:第一,我们在谈论威权政府合法性时的层级一般是中央政府,而研究对象往往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绩效合法性和地方政府的绩效合法性有没有关联?第二,研究把推迟政策实施也视为民众抗争成功,那么延误时间的长短是否应该有所区分?第三,研究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是有无媒体报导,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如何采集到环境抗争事件的相关信息?
对此,杨鸣宇博士回应道:首先,文章的关注重点不是绩效合法性,只是在文末引出的一点讨论;其次,无论政策的实施时间推迟了多久,我们都视之为公众成功影响的产物;最后,研究过程中考虑过对媒体的类型、影响力进行细分,但是由于操作性问题不得不放弃。媒体的编码都是1,即所有事件都是有媒体报导的。
(行政管理研究所 张盛供稿)

